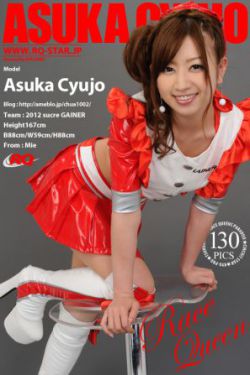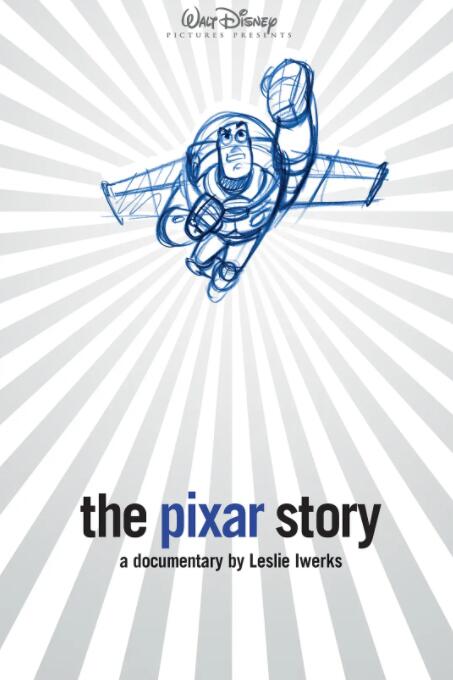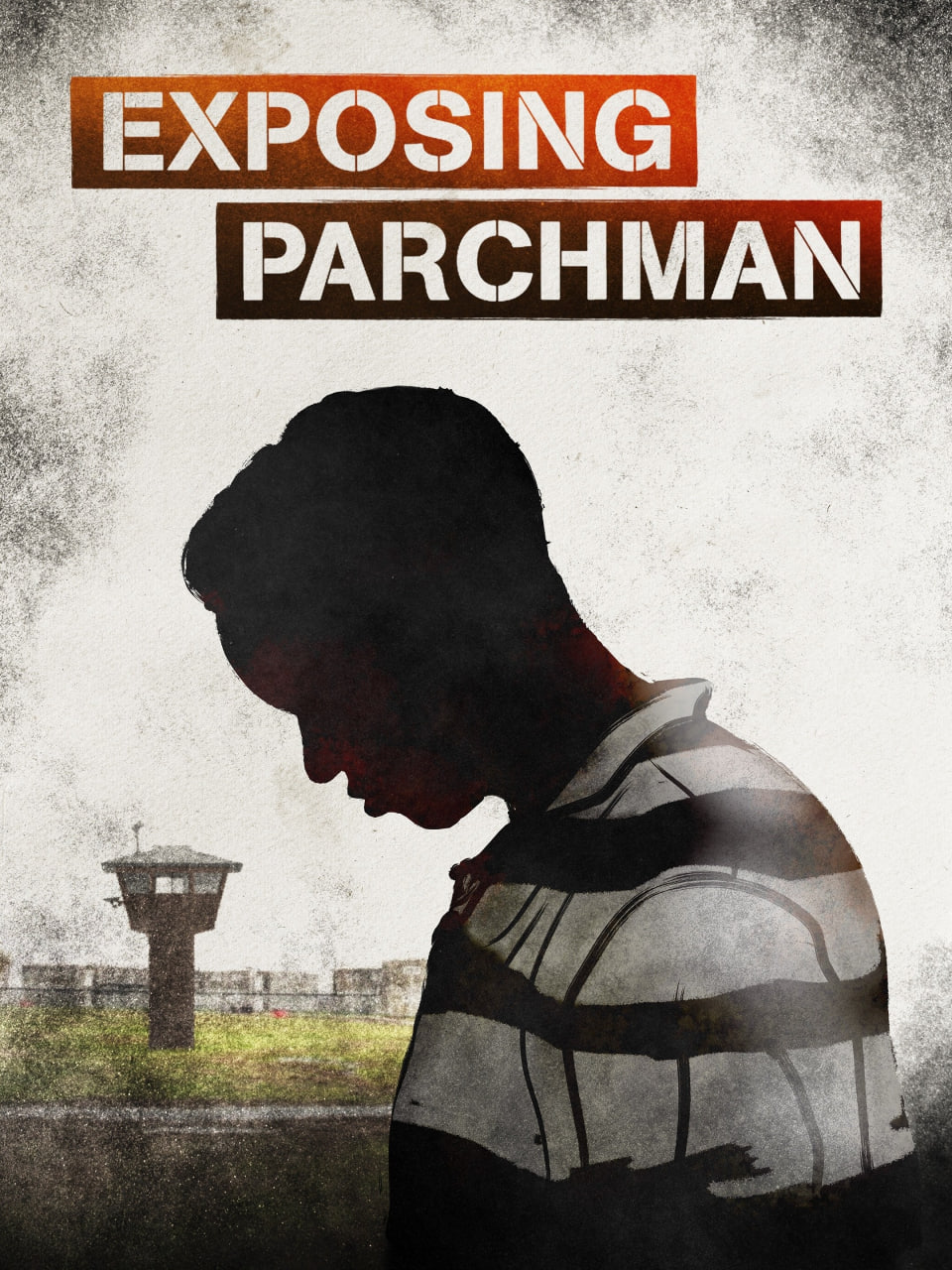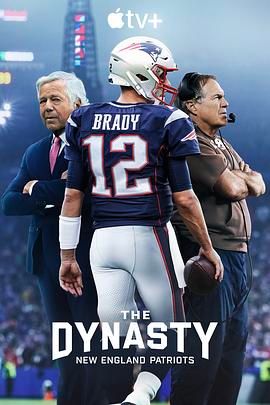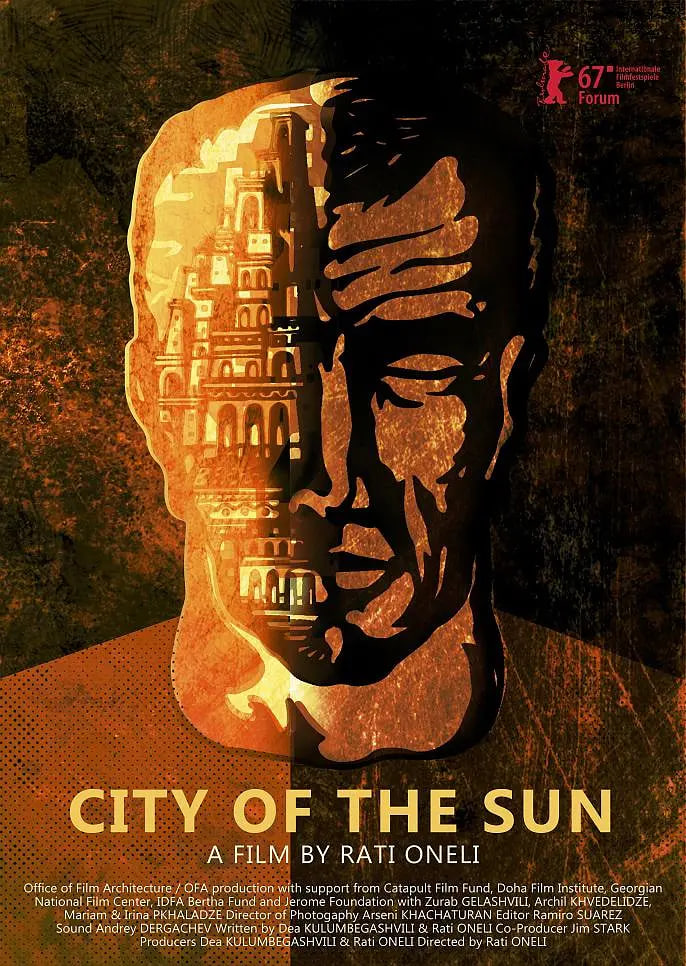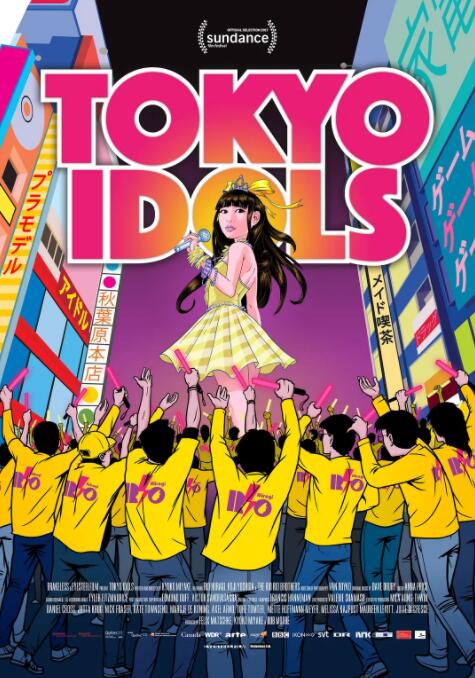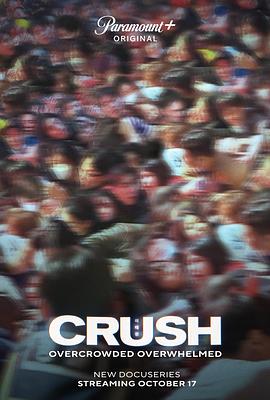豆瓣資源
豆瓣資源
 劇情簡介
劇情簡介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不过最最让人觉得厉害的是,在那里很多中国人都是用英语交流的。你说你要练英文的话你和新西兰人去练啊(✈),你(🔥)两(🤰)个(🥫)中(✴)国(📱)人有什么东西不得不用英语来说的?
这还不是最尴尬的,最尴尬的是此人吃完饭踢一场球回来,看见老夏,依旧说:老夏,发车啊?
于是我充满激情从上海到北京,然后坐火车到野山,去体育场踢了一场球,然后找了个宾馆住下,每天去学院里寻找最后一天看见的穿黑色衣服的漂亮长发姑娘(🥤),后(🧠)来(⏹)我(😉)发(🎙)现(🔚)就算她出现在我面前我也未必能够认出,她可能已经剪过头发,换过衣服,不像我看到的那般漂亮,所以只好扩大范围,去掉条件黑、长发、漂亮,觉得这样把握大些,不幸发现,去掉了这三个条件以后,我所寻找的仅仅是一个穿衣服的姑娘。
我说:行啊,听说你在三环里面买了个房子?
路上我(🈂)疑(🤭)惑(🐭)的(🔶)是(🔹)为(📴)什么一样的艺术,人家可以卖艺,而我写作却想卖也卖不了,人家往路边一坐唱几首歌就是穷困的艺术家,而我往路边一坐就是乞丐。答案是:他所学的东西不是每个人都会的,而我所会的东西是每个人不用学都会的。
他们会说:我去新西兰主要是因为那里的空气好。
中国人首先就没(🏄)有(⏮)彻(⏸)底(🕵)弄(🕝)明(🌪)白(🎤),学习和上学,教育和教材完全是两个概念。学习未必要在学校里学,而在学校里往往不是在学习。
我说:只要你能想出来,没有配件我们可以帮你定做。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五月。老夏和人飙车不幸撞倒路人,结果是大家各躺医院两个月,而老夏介绍的四部跑车之中已经有三部只剩下(🐼)车(🎓)架(🎼),其(💵)中(🌍)一(🀄)部是一个家伙带着自己的女朋友从桥上下来,以超过一百九十迈的速度撞上隔离带,比翼双飞,成为冤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