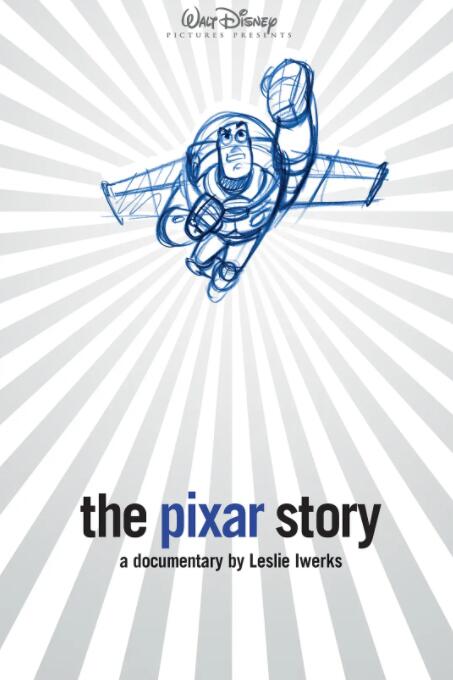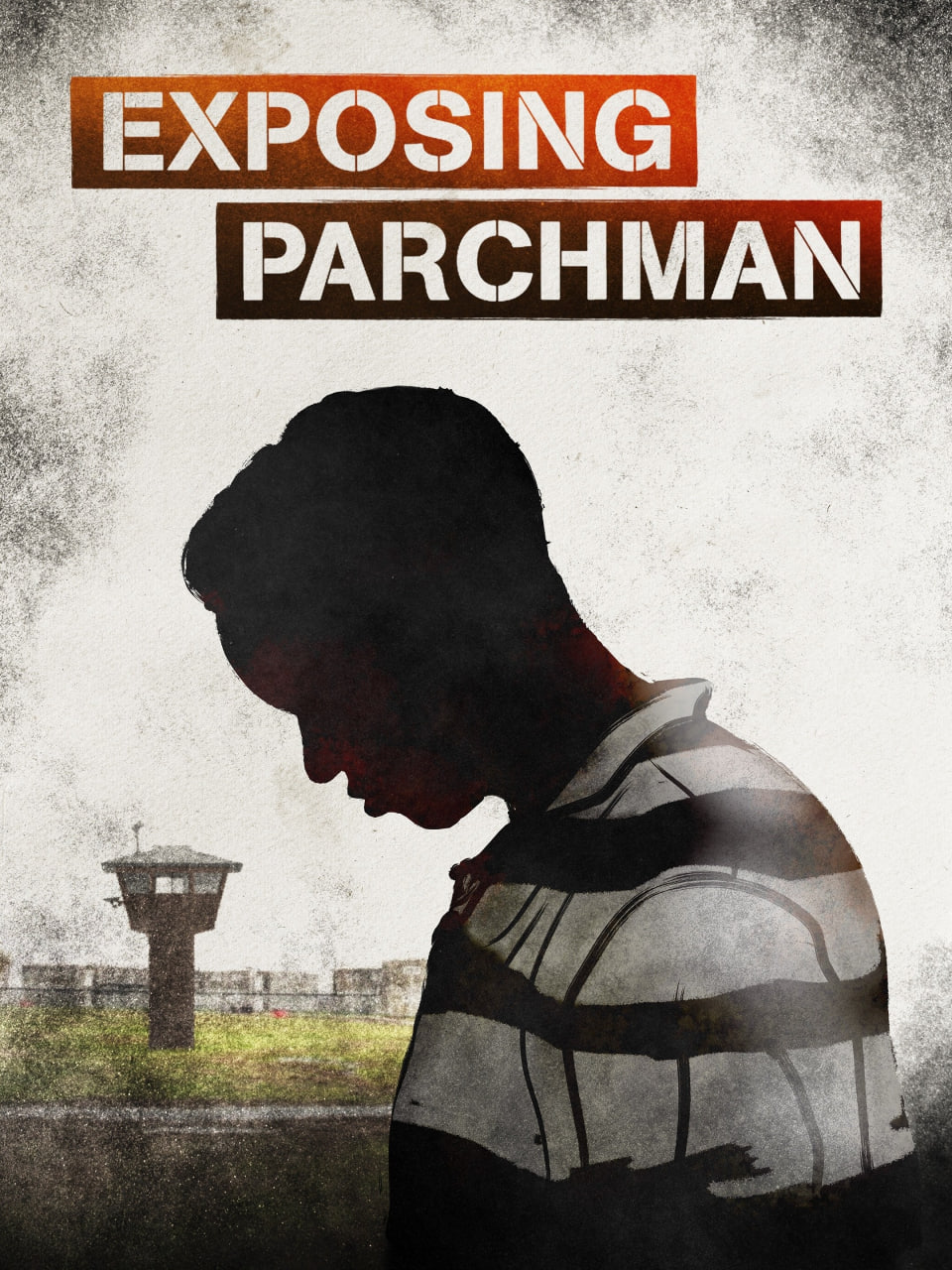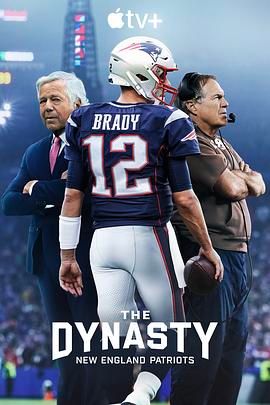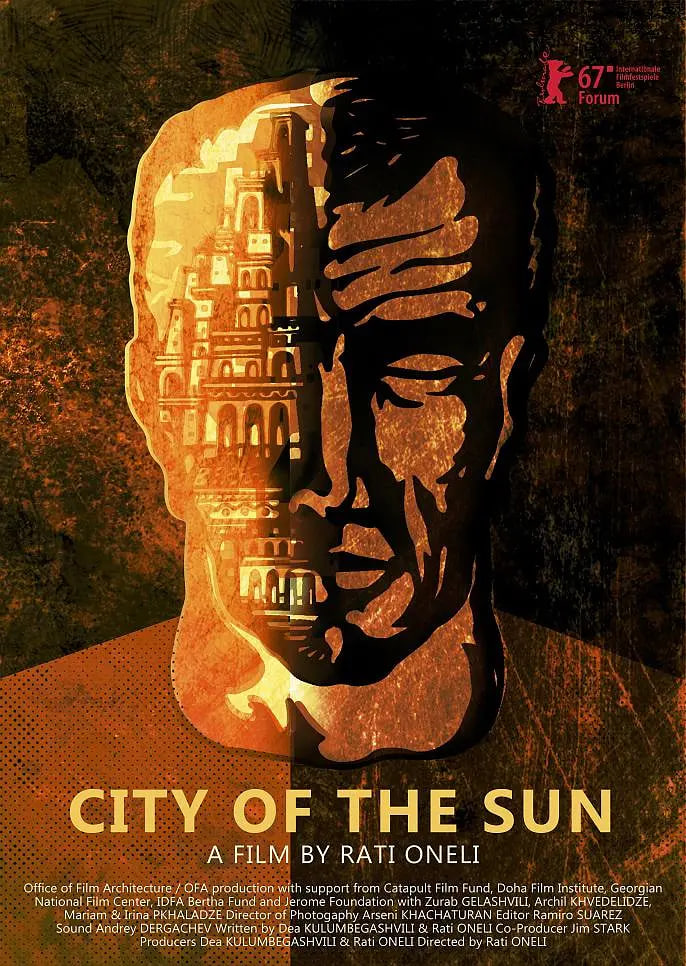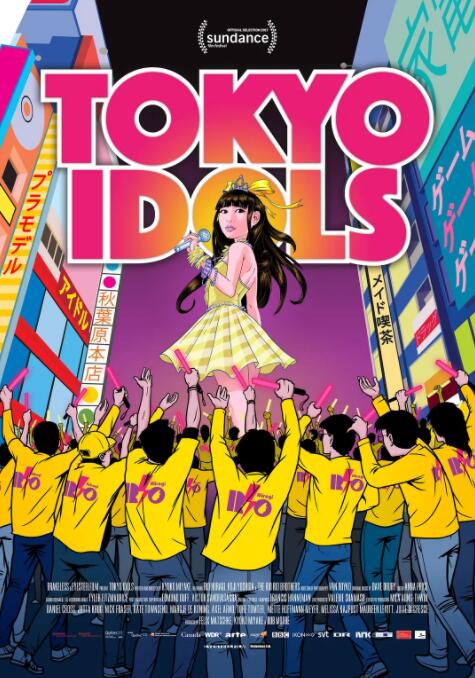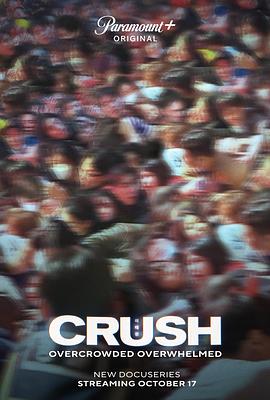豆瓣資源
豆瓣資源
 劇情簡介
劇情簡介
我在北京时候的一天晚上,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外地的读者,说看了我的新书,觉得很退步,我说其实是(😡)我进步太多,小说就是生活,我在学校外面过了三年的生活,而你(😗)们的变化可能仅仅是从高一变成了高三,偶像(⭐)从张信哲变成了(🎈)F4而已,所以根本不在一个欣赏的层次上。我总不(🤽)能每本书都上学啊几班啊的,我写东西只能考虑到我的兴趣而(😫)不能考虑到你们的兴趣。这是一种风格。
当时我对这样的泡妞方(🧞)式不屑一顾,觉得这些都是八十年代的东西,一切都要标新立异(🌜),不能在你做出一个举动以后让对方猜到你的(✂)下一个动作。
到了(😻)上海以后,我借钱在郊区租了一个房间,开始正(⛱)儿八经从事文学创作,想要用稿费生活,每天白天就把自己憋在(🍡)家里拼命写东西,一个礼拜里面一共写了三个小说,全投给了《小(🛤)说界》,结果没有音讯,而我所有的文学激情都耗费在这三个小说(🎩)里面。
校警说:这个是学校的规定,总之你别发(🚫)动这车,其他的我(🏺)就不管了。
在做中央台一个叫《对话》的节目的时(🤣)候,他们请了两个,听名字像两兄弟,说话的路数是这样的:一个(🕗)开口就是——这个问题在××学上叫做××××,另外一个一(📯)开口就是——这样的问题在国外是××××××,基本上每个(🚂)说话没有半个钟头打不住,并且两人有互相比(❓)谁的废话多的(🛫)趋(🐮)势。北京台一个名字我忘了的节目请了很多权(🐜)威,这是我记忆比较深刻的节目,一些平时看来很有风度的人在(🦋)不知道我书皮颜色的情况下大谈我的文学水平,被指出后露出(🎬)无耻模样。
生活中有过多的沉重,终于有一天,能和她一起无拘无(🥪)束地疾驰在无人的地方,真是备感轻松和解脱(🐛)。
不过最最让人(🐲)觉得厉害的是,在那里很多中国人都是用英语交(💥)流的。你说你要练英文的话你和新西兰人去练啊,你两个中国人(📠)有什么东西不得不用英语来说的?
那人一拍机盖说:好,哥们,那(〰)就帮我改个法拉利吧。
我的特长是几乎每天都要因为不知名的(🍒)原因磨蹭到天亮睡觉。醒来的时候肚子又饿了(👎),便考虑去什么(🍿)地方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