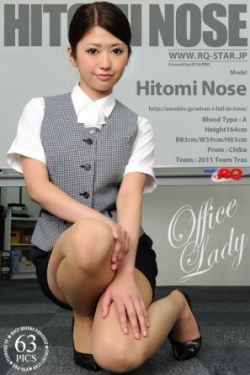豆瓣資源
豆瓣資源
 劇情簡介
劇情簡介
我的朋友们都说(😆),在新西兰你说你是中国人人家会对你的态度不好。不幸的是,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也不见得好到什么地方去。而我怀疑在那里中国人看不起的也是中国人,因为新西兰中国人太多了(📟),没什么本事的,家里有点钱但又没有很多钱的,想先出国混张文凭的,想(🧛)找(📹)个外国人嫁了的,大部分都送到新西兰去(👶)了。所以那里的中国人素质不见得高。从他们开的车的款式就可以看出(😟)来(🍻)。
于是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大包围,换了个大尾翼,车主看过以后十分满意,付好钱就开出去了,看着车子缓缓开远,我(🛏)朋(💒)友感叹道:改得真他妈像个棺材。
最后在我们的百般解说下他终于(🕳)放(🖼)弃了要把桑塔那改成法拉利模样的念头(🚆),因为我朋友说:行,没问题,就是先得削扁你的车头,然后割了你的车顶(🔴),割(🚭)掉两个分米,然后放低避震一个分米,车身得砸了重新做,尾巴太长得割了,也就是三十四万吧,如果要改的话就在(🙉)这(🕢)纸上签个字吧。
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
年少时,我喜欢去游戏中心玩赛车游戏。因为那可以不用面对后果,撞车既不会被送(⏲)进(💚)医院,也不需要金钱赔偿。后来长大了,自己驾车外出,才明白了安全的(🥅)重(🦕)要。于是,连玩游戏机都很小心,尽量避免碰(🏺)到别的车,这样即使最刺激的赛车游戏也变得乏味直到和她坐上FTO的那(👲)夜(📐)。
年少的时候常常想能开一辆敞篷车又带着自己喜欢的人在满是落叶的山路上慢慢,可是现在我发现这是很难(🤯)的(👱)。因为首先开着敞篷车的时候旁边没有自己喜欢的姑娘,而有自己喜(🎫)欢(🔠)的姑娘在边上的时候又没开敞篷车,有敞(🥟)篷的车和自己喜欢的姑娘的时候偏偏又只能被堵车在城里。然后随着(🌲)时(📟)间过去,这样的冲动也越来越少,不像上学的时候,觉得可以为一个姑娘付出一切——对了,甚至还有生命。
我在北(🌠)京(🅰)时候的一天晚上,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外地的读者,说看了我的新书,觉得很退步,我说其实是我进步太多,小说就(🥛)是生活,我在学校外面过了三年的生活,而你们的变化可能仅仅是从高(😍)一(🔏)变成了高三,偶像从张信哲变成了F4而已,所以根本不在一个欣赏的层次上。我总不能每本书都上学啊几班啊的,我(🎋)写(🌹)东西只能考虑到我的兴趣而不能考虑到你们的兴趣。这是一种风格。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北京一直考虑要一个越(🤢)野车。
这天老夏将车拉到一百二十迈,这个速度下大家都是眼泪横飞,不(👬)明(🚒)真相的人肯定以为这两个傻×开车都能开得感动得哭出来。正当我们以为我们是这条马路上飞得最快的人的(😣)时(❔)候,听见远方传来涡轮增压引擎的吼叫声,老夏稍微减慢速度说:回头看看是个什么东西?
第二笔生意是一部桑(😐)塔那,车主专程从南京赶过来,听说这里可以改车,兴奋得不得了,说:你(💛)看(🈷)我这车能改成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