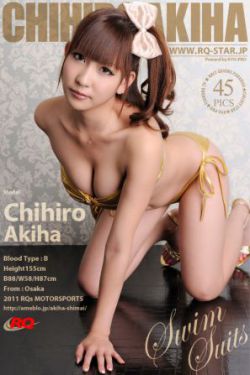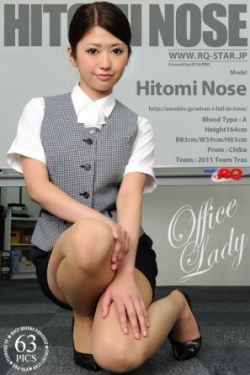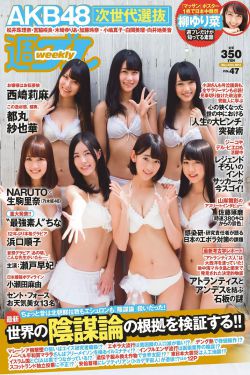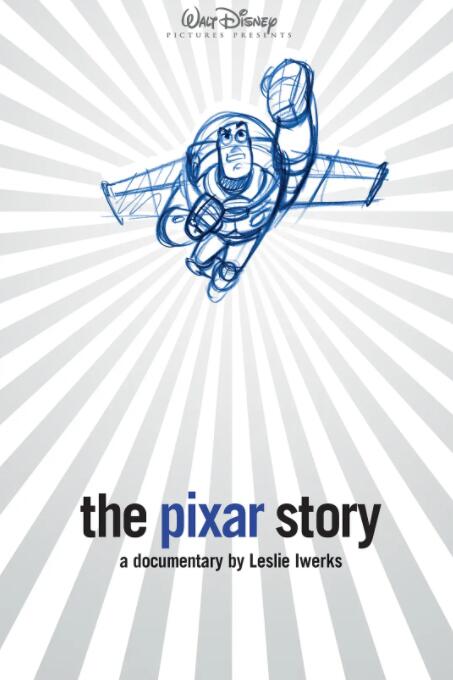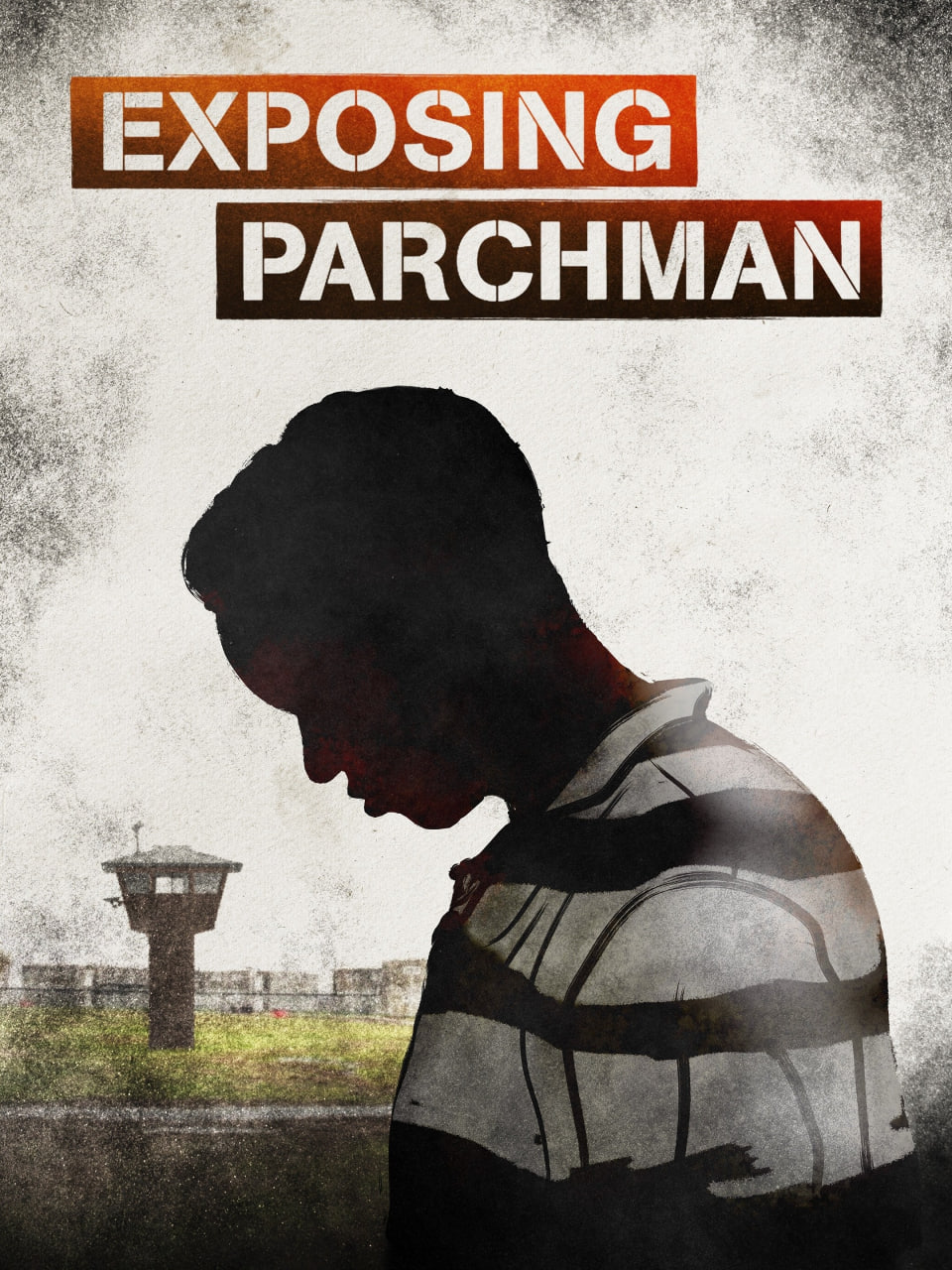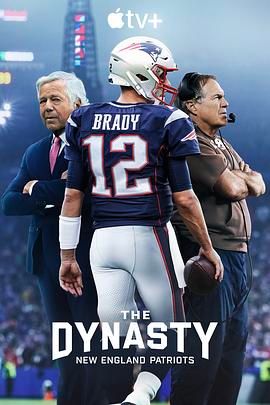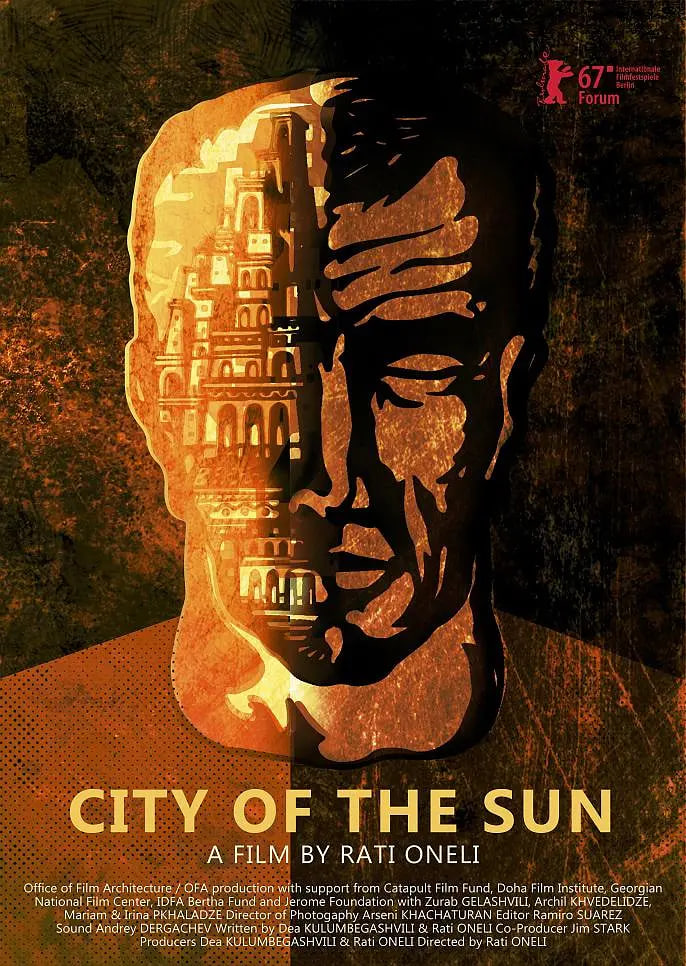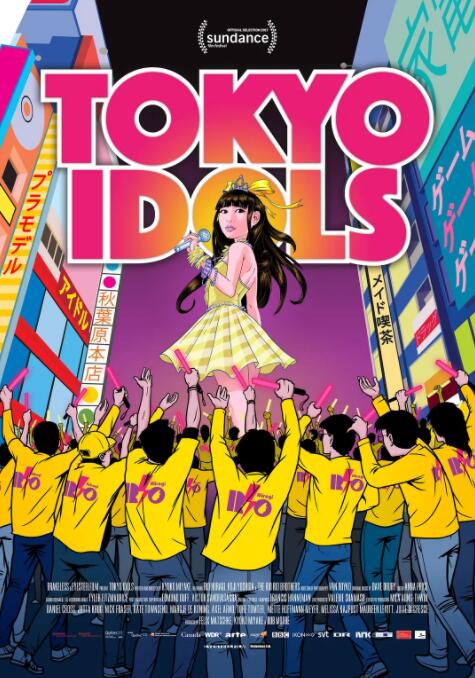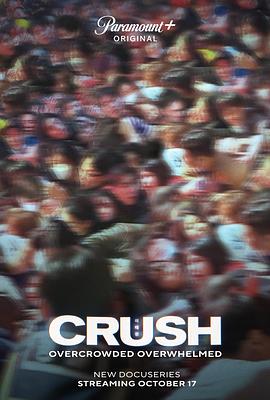豆瓣資源
豆瓣資源
 劇情簡(jiǎn)介
劇情簡(jiǎn)介
同时间看见一个广告,什(🚹)么牌子不记得了,具体就知道一个人飞(👂)奔入水中,广告语是生活充满激情。
在做(🚜)中央台一个叫《对话》的节目的时候,他们(🏜)请了两个,听名字像两兄弟,说话的路数(👓)是这样的:一个开口就是——这个问(📹)题在××学上叫做××××,另外一个一开口就是——这样的问(💶)题在国外是××××××,基本上每个(🙂)说话没有半个钟头打不住,并且两人有(🎮)互相比谁的废话多的趋势。北京台一个(🙈)名字我忘了的节目请了很多权威,这是(🚊)我记忆比较深刻的节目,一些平时看来(🦗)很有风度的人在不知道我书皮颜色的情况下大谈我的文学水平,被指出后露出无耻模样。
我在北京时候(⏪)的一天晚上,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外地(🆎)的读者,说看了我的新书,觉得很退步,我(💽)说其实是我进步太多,小说就是生活,我(🐏)在学校外面过了三年的生活,而你们的(👧)变化可能仅仅是从高一变成了高三,偶(✨)像从张信哲变成了F4而已,所以根本不在一个欣赏的层次上。我总不能每本书都上学啊几班啊的,我写东西(🚓)只能考虑到我的兴趣而不能考虑到你(📎)们的兴趣。这是一种风格。
这样一直维持(🕶)到那个杂志组织一个笔会为止,到场的(💂)不是骗子就是无赖,我在那儿认识了一(🎩)个叫老枪的家伙,我们两人臭味相投,我(📖)在他的推荐下开始一起帮盗版商仿冒名家作品。
而那些学文科的,比如什么摄影、导演、古文、文学批(🚁)评等等(尤其是文学类)学科的人,自豪地(🤔)拿出博士甚至还加一个后的文凭的时(🕣)候,并告诉人们在学校里已经学了二十(🍸)年的时候,其愚昧的程度不亚于一个人(🐴)自豪地宣称自己在驾校里已经开了二(🍭)十年的车。
关于书名为什么叫这个我也不知道,书名就像人名一样,只要听着顺耳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有意(🈺)义或者代表什么,就好比如果《三重门》叫(🧞)《挪威的森林》,《挪威的森林》叫《巴黎圣母院(👤)》,《巴黎圣母院》叫《三重门》,那自然也会有人(🧗)觉得不错并展开丰富联想。所以,书名没(👣)有意义。 -
我上海住的地方到我父母这里(🔣)经过一条国道,这条国道常年大修,每次修路一般都要死掉几个人。但是这条路却从来不见平整过。这里不(🚭)是批评修路的人,他们非常勤奋,每次看(♑)见他们总是忙得大汗淋漓。就是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而已。
我最后一次见老夏(🥄)是在医院里。当时我买去一袋苹果,老夏(🌃)说,终于有人来看我了。在探望过程中他(🛸)多次表达了对我的感谢,表示如果以后还能混出来一定给我很多好处,最后还说出一句很让我感动的话(📌):作家是不需要文凭的。我本以为他会(🍍)说走私是不需要文凭的。
以后我每次听(🐶)到有人说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的时候(🌼),我总是不会感到义愤填膺,因为这世界(🔼)上不会有莫名其妙的看不起,外国人不(🥋)会因为中国人穷而看不起,因为穷的人都留在中国了,能出国会穷(🦍)到什么地方去?